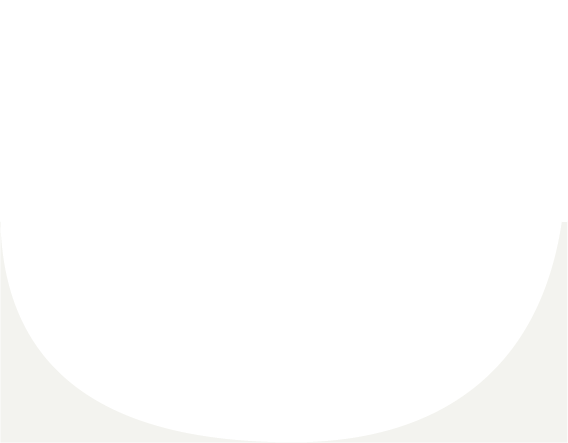works
文學獎專區
歷年資料

人生幾何
台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
陳聖文
得獎感言
散文,我是第一次嘗試,不得不說實際存在的東西真的很難描寫。現實中不存在劇情主軸、不存在人物設定,一切是這樣恰到好處地荒誕無序。雖然我拙劣的文字只有得到佳作,我還是很慶幸自己有所嘗試,這篇文章近似於日記,在我最迷惘煩悶的日子裡,允許了美的追求與存在。
感謝楊德威、許明志、袁銘德、林倩如四位老師,因為有你們的鼓舞我才不至於對未來過分不安。
特別感謝藍色時期的作者山口飛翔,正是讀了這本漫畫我才提起勇氣創作。
人生幾何 ◎ 陳聖文
幾何的第一條定理:任兩個相異點可以決定一直線。沒有例外,單純又明快。
這是小學生都會的作題技巧。一個點既沒有方向性也無長短,不好算,把它和另一點連起來比較方便。比如把線AB延伸出去,和線CD的交點便是答案。又或者是把學測分數與志願序連起,投影到生命的常期,隱約就是一生。
填卡、檢查、收卷,打鐘的時間恰是填完答案的下一秒,心跳和鐘聲搶著衝撞耳膜。冷靜,我強壓下要撕裂身體的脈動。這只是模擬考,考得不好還能拿「模擬」二字當藉口,還能當一會鴕鳥。死線還沒到。
死線正寫在黑板右上角,稍黯淡的粉筆字在墨綠版面上。「60」。正確來說是59天,今天不過忘了換。黑板上怎麼寫其實也不重要,死線不斷迫近,有沒有注意都一樣。每一天佔生命的份量理應不同,考生的步調不然,今天兩百題明天再兩百,每一天短暫得一樣漫長,像定時的幻燈片,不予停留、禁絕牽掛。
考完數學後是自然,中間有短暫的歇息。班上開始聒噪,我往外頭散心。試卷使人心煩,戰間期總得找些閒話,才容易忽視不安。倚在圍欄邊,同學問我考得怎麼樣,我說要看線在哪裡。「那你的線在哪?」他問,我說我不知道。我是一個點,受困於自由,遲遲不敢選出另一個點,沒能奢求一條線的單純明快。輕嘆口氣我說「我還在找另一點。」
※
自然試卷發下,帶種莫名的懷舊。
曾經,我是個理科生,筆直的一條線。國中會考還沒倒數,就在妄想錄取科學班。當時並不迷惘,追逐目標時最不缺的就是理由。目標是精神食糧,助我挑燈夜讀,心急無措時總有個標竿指路,凝視便無迷茫。那標竿引我在參考書局、K書中心、補習班間折返,卻不折騰,因為有了一條我隨意地稱為夢想的線。
大概是瞪視那標竿太久,最後它不過是個地標,刻上的只有「到此一遊」卻沒有揭示下一步的方位。轉運站成了終點,抵達後驀地再前盼,卻像是莫名翻到了童話的完結頁。夢想塌了,假設它曾挺立過。拚死拚活跟數理搏鬥了一年,居然不知道何去何從,真想問自己身為理科生的理性何在。
在科學班一天天浸在唯物的世界,不難體會何謂虛無。曾有一次讀了人工智慧訓練理論,看單調的位元如何發展出思考的潛質;而我在應著題目的要求計算,機械性地,理性地。又聽說理性的人類在無序的世界,只能碰撞出荒謬的回聲。物理課老師在講著名的波粒二象性時,說一個理應只有一點的粒子,在通過細絲一般的狹縫後卻能顯現波的性質。只有在被觀測時,所有的可能性才會收束回到一個點,落在屏幕上。我暗自揣想,在撞上屏幕,所有可能性塌陷成為既定的點的瞬間,那粒子是否也會感到不安。
化學實驗室裡製備阿斯匹靈,秤得止痛的劑量卻飄飄然感受不到生命的重量。實驗完,產物迴歸直線相關係數甚高,幾乎沒有偏差。任兩個相異點仍舊能決定一條線。線是直的,人卻不是。也是在這時我才明白,不論是多麼精準的計算,始終是無法證明荒誕的生命裡不規則排列的種種疑問。我起了轉組的念頭。
※
作文紙上爬滿網格,文字苟且,或寄生或擱淺在網間。題目是「錯過」,連結甲文或乙文。這模式我早已熟習:不要偏題,答案畢竟是攀附在題目上;像在清單上打勾,要展現多面向的能力。規劃好架構,一愣間悵然若失,不知道錯過甚麼。莫慌,所幸我早有預備,錦囊裡取出精心編造的故事,不多想地下筆便是,結尾要陽光正向,佯裝自己是全知的局外人,早已看破困惑。
還記得剛轉到文組,親戚不解地看向我,像審視被告席上的叛逃者,像是要問我為什麼要跟你的大好前程過不去。爸媽做我的發言人,也是袒護,說文組也有高薪的科系,財金或法律之類,儘管我到了文組並不是為了讀這些科系。親戚們似乎稍能認同,見戰況舒緩我也沒再吭聲,只是默認,打寂靜的拖延戰。他人即地獄,所幸審判日的死線還沒到,還能假裝身處天堂。哪怕生而為人不是走直線,也能夠這樣假裝。
※
考社會,有人說要訣只是「背多分」,有背就有分。那分明是歪理,多少題目刷下來,重點其實是在找那一條線。任何的光譜都能找到條線切割,那是衝突的最前線,線的兩側各貼了某種標籤:資方與勞方、人類與自然、左派與右派、妄想與實踐、好學生與壞學生、高薪低薪云云。而最重要的那條線,是考或不考。猶太、吉普賽、烏克蘭、同性戀,世界無限寬闊,課本偶爾收錄,三維的世界壓上二維的試卷,批量打印出一維的思維。
曾經有那麼一次,在家裡說想讀文學院,回覆是扎人的沉默。雙親的眼神閃爍,怕傷及孩子的自尊卻又是不可置信,好似我所吐出的是甚麼不得體的穢語,像是要在我身上尋回當初那個盯著電腦螢幕癡笑的孩子。接踵而來的問題也不令人意外,「讀哲學或文學要幹嘛?」。反駁如「那活著又是要幹嘛?」只是鯁在咽喉,因為他們說的有理。養育之恩重如山,溫室裡的花朵竟敢把自己看作籠中鳥,執拗地想飛,不過是不自知的伊卡洛斯。
他們沒有回應,我至今也未再提起。我不敢面對他們的困惑,正如我無能處理自己的,或許是我辜負了父母對成功的期待,死腦筋地偏離了安穩富庶的正道。原來兩個點之間,可以連一條線也描摹不出,又或許正是某條過分纖細的直線切割了一切。
※
早已聽膩的鐘聲響起,這是今天的最後一次鐘響。在孔孟、牛頓、伏爾泰的夾擊下,又一日僥倖生還。冷硬的木製課桌椅沒有記起我的形狀,每條稜線仍是方正、筆直,懲罰坐姿的歪曲。筆直的時針、筆直的門扉、筆直的牆,被這樣筆直的環境所環繞,作為一個不規則的人總是難以將自己嵌入。
夜自習後返家,在早已走慣的路口前等紅綠燈。亮紅的小人舉著時間,從60開始倒數,一秒又一秒,時間是我和現實間少數互通的頻率。時間持續地流逝,眼前理當靜止的斑馬線竟順著時間的流動,好似要一公分一公分地撲向我。我狠狠地瞪著一條又一條的斑馬線,好像那樣拚了命地以目光灼燒無物的空氣,就能使其退卻一般。
我瞇起眼睛,像在道路的更前方,有更加開闊的甚麼在等待著。每每正要以目光窮極天際線的彼端,一切卻又模糊了。時間持續地流逝,在適當或不適當的時間,不論如何都要跨步,向前。幾隻麻雀款款地飛過,俯瞰扎根於水泥地面的我。筆直的道路遽然模糊了起來,難以想像那樣模糊的柏油與那樣朦朧的地平線要如何相交。
柔和斜陽灑入路口,和著機車排的廢氣,一片浪漫混濁的塵囂。
任兩個相異點可以決定一直線,平面上直線太多,無法細數。
其中唯一的通則,是都看不見盡頭。
評審評語 ◎阿盛
一個理科生轉讀文科,作者描述了心理轉折與他人的反應,用了幾何定理來比喻,這樣的手法很好。文字技巧很不錯,有創意,往往能令讀者會心一笑。這篇作品同時也道出了許多年輕學生的心聲——選擇的難題。結尾短短幾句卻相當有力,足以發人省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