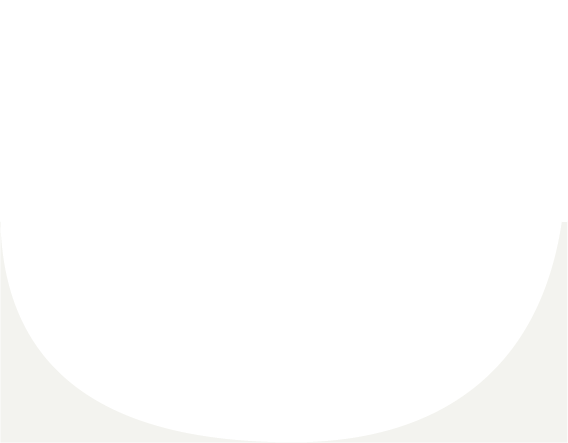works
文學獎專區
歷年資料

嵐
國立嘉義高級中學
黃奕豪
得獎感言
有關家人的題材,是房間某個不常開的抽屜裡,藏匿著的一紙羞怯,柔軟、敏感,偶爾卻不小心遺忘它的存在。
謝謝去年的我在居家隔離時,發現這塊晦暗的角落並書寫,沒經多少潤飾,就一氣呵成地提交稿件,也該感謝命運、感謝父母、感謝老師、煙穗編輯與朋友們,感謝所有人。話說,這是我第一次得文學獎,然後感謝嘉義高中語資班,希望有更多學生加入,也希望嘉中多多鼓勵創作,感恩。
嵐 ◎黃奕豪
我與父親的世界,隔了片濃霧。
這場霧是從何時起的?
我舉起手指頭數著,舉起一隻、兩隻……,嘴裡也默念著一年、兩年……才知道那是雙手也算不完的數量,這場霧早已持續了數不清的年歲。我遺忘是什麼時候開始和父親產生隔閡的,更不知道結束的日子,會落在年曆上的哪一天。
別人同我提起家人,第一個浮現我腦海的,往往會是織著衣服的母親。因我總笨手笨腳,跌倒擦傷這檔事可難不倒我,難倒我的是縫補那破損的衣服,這樣的「重責大任」無可奈何地擔到了善縫補的母親身上。填補我破洞的襯衫時,她常唸叨著我的不小心,一邊在衣衫缺口上,填上一塊簡樸的安心。我瞅著縫補衣物的母親,總覺得她的一針一線,織的是一個家的平靜與和諧,若沒有她,家人只會是支離破碎的布料。一個家的完整,都是由她接縫起來的。
母親是狂野與細膩並存的風。我想翱翔到哪個新領域,她通常二話不說便會成為托著我飛翔的風。她習慣無聲的支持,在我被壓力追著向前衝刺時,常看見她靜默的貼心:那書架上莫名多了的維生素C(知道我不愛吞藥,還刻意買了摻糖的),她三言兩語帶過,只說要記得吃。對峙還未達成的目標時,我靜靜嚐著暈染在我嘴裡的甜,那份屬於母親的支持與溫情。母親買了兩罐維生素C,另一罐是給父親的。然而對父親來說,菸才是他的保健食品,那份溫情好像硬生生變成了不領情。
別人提起自己的父親時,眼神裡都多了那麼點依賴與敬仰。他們描述自己的父親,都讓我聯想到山——高聳壯麗,讓人得以依靠、崇拜的山。有人說起他的父親是法官,常常和他討論社會案件,他父親會問那同學會怎麼判決?彼此之間爭論不休。在提起他父親時,我看見了他的眼睛燃起了繁星點點,瞳孔隨著光影一張一縮,像把我生吞活剝的黑洞,可我心甘情願地被吸入。心裡明知道這樣的念想極度差勁,卻還是不禁泛起一絲絲羨慕,像春風吹又生的雜草,這樣的念頭消去又瘋長,反反覆覆,好像在控訴我,心裡頭最真實的欣羨,扎得太深。
對我而言,父親有時會自私地成為撕裂和諧的慣犯。他時常是與母親吵架時的導火線,在兩人話語逐漸摩擦時,母親就會要我躲回房間,以為我躲在自己房間裡,就能緊抓殘存的平靜。這是母親難得的粗心,她不知道,他們的爭吵會吞沒整棟房子,那些刺耳的喧囂依舊會從門縫滲入,然後殘忍地虐待我。雙方嘶吼聲讓我房間的牆上,好像長出駭人的裂線,感覺下一秒,整個家和我的心房就會應聲而垮。
我的父親有時像不負責任的孩子,爭吵的導火線,往往是父親厭倦了工作僅此。我對這樣的父親感到啞口無言,卻又無可奈何,面對面時,彼此活成兩座沉默的石像,想說些什麼,最後的結局都是無聲的散場。若全天下的父親都能比喻成山的話,那時,我理解的父親就是自私壓垮母親的山,或許就在那時,我與父親之間,萌生看不清彼此的嵐。
我與父親漸漸活在兩條平行線,連母親也縫合不了我與父親之間的生疏,不,該這麼說,是就連母親沒察覺到,我與父親的關係正在變質。變化在悄然發酵著,就像時間一樣,也無聲地把父親形塑成我不認識的樣子,他的樣子依舊,然而他的心,我卻已經看不清了,如「最熟悉的陌生人」。那是我認為最心碎的詞彙,幾年來這個忍受風吹雨打的家始終不變,父親他卻說變就變。
父母的爭吵像潮汐一般,時候高漲,時候消退。那陣子幾個月就突發的爭吵,讓恐慌統治了我,父母沒能察覺我心緒紛亂是源自於他們,只認為我是在征服課業的路上失足了,才敏感地像隻警戒的貓。
看他們時好時壞的關係,懷疑不禁擴散在我胸臆間,哪個才是真實的他們?我不理解他們的世界,因為父母親始終把我攔在孩童的樂園裡,以為我能天真無邪地活著。然而事實是,被隔絕在外的我反覆猜忌:他們是怕我擔心而開始角色扮演,還是兩人在關係上真的做出讓步?
為了緩解我因為「課業壓力」而擺盪不安的情緒,母親決定拉著我與父親去旅行。她硬是在年曆上的某個假日裡用紅筆圈了一天,要我和父親把那天的行程空出來。想當然耳,要父親和我們一同去,有較大部分是因為我們缺了個熟山路的司機。父親一方面在都市做裝修鐵門的工作,在「菁仔期」時,也要回山區的老家幫忙收採檳榔,奔波多地的檳榔產區,全臺沒有一條山路是他不熟悉的。他是山的孩子。
自從五歲我搬離山間老家,只有在每年除夕夜裡罕見地和山團圓,我和它就像是鮮少往來的親戚,對話裡只有乾笑與生疏交雜的寒暄,最後以靜默收尾,剩下的只有隨海拔升高鑽入我耳裡的鳴聲,我靠在車窗上,伴著一車子的沉默入睡。
我們的目的地到了,在我叫不出名字的山頂。景色像是塑料,死板的雲、單一色調的藍天、向下滾去的茶園、刺眼的白日高掛正空,把父母親的臉都照得更加黯淡,酸汗沁出體表,讓襯衫緊緊依附著身體,像擺脫不了的惆悵。即便我們逃到這麼高的地方,那團都市的烏煙瘴氣依舊纏著我們腳跟。胡亂拍了幾張曝光的照片,父親見天色不大對勁,便要我們立馬下山。母親一直都不發一語,漸漸,我也看不清母親心裡的那片朦朧了。
果真如父親預料的那樣,在山中的天氣瞬息萬變,我們掉入了環繞大霧的山林,在公路兩側都是隱隱綽綽的綠色,世界被潑成一片混濁的白。那對我來說是這趟旅途的豔遇,畢竟我已經十多年沒看過山裡的大霧,我嚷嚷著能不能下去拍照?
父親應允說好,但是不能太久。父母親靠在車旁,彼此不發一語。我提著手機,在離他們不遠處,拍攝公路邊的鳥,牠們圓滾的身體並肩跳著,共三隻,在霧間逡巡遊戲。剎時,有那麼一隻倏地飛遠,被那片迷幻的大霧盡為所吞,兩隻陪在牠身旁的鳥目送牠的離去。
我回頭望靠在車旁的雙親,我與他們的世界都隔了層霧。他們會不會其實也這樣認為:我與他們的世界越來越遠了。
我緩緩走近,卻看父親的臉龐染上的潮濕。他生疏地向我解釋,那只是霧太濃罷了。
我還沒反應過來,那天一直沉默的母親便先開口,問父親:「你覺得飛走的那隻鳥會飛回來嗎?」
父親愣了愣,思量了一陣,「牠會回來,因為牠知道有兩隻鳥還在原地等牠。」
母親嘆了口氣,「你把工作辭掉吧,專心去老家那邊幫工。」說完便上了車,和我一起。
我看見門外的父親燃起了一捲菸,燃起零星的寂寞,菸煙與山嵐融為一體。
我看見車內的母親眼睛泛起了淡紅色,但嘴裡掛著往常的平靜。
我看見窗外的公路邊飛回一隻鳥,是父親,也是我。
我看見了我的自私。
忘了人,都可以擁有自己想要的目標。
評審評語 ◎阿盛
描寫親人之間情感曲折變化,觀察很細心,筆調直白自然,沒有過多的修飾,譬喻也恰當。刻畫父親與母親的性格相當成功,雖是平常家庭的小事,但選材處理得恨恰當,掌握分寸得宜,敘述因此不至於瑣碎,這一點很難得,能令人感受到作者真實的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