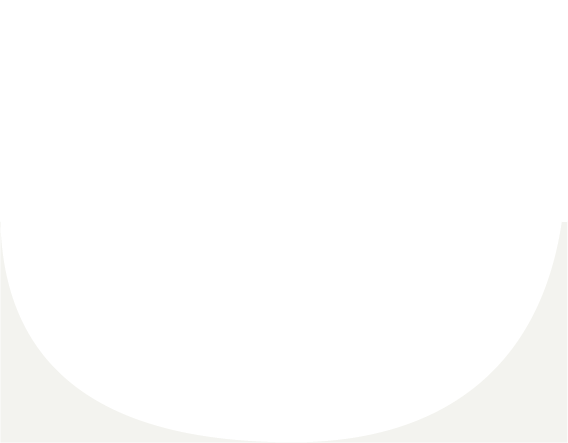works
文學獎專區
歷年資料

雜貨店
中壢高中
陳振瑋
舅舅家的一樓是雜貨店,販售各種文具、海報、作業本、玩具模型,只是都相當過時,舅舅也明白,這些泛黃的雜物堆放著也只是淪為灰塵的溫床,但他並未將它們扔掉,時代的眼淚就這樣一直陳列在店內。
舅舅一家與外婆同居,從前,父母親與我幾乎每週六都會探訪外婆,舅舅的雜貨店因此成為我所熟悉的空間,三十餘坪大的雜貨店裡,門內的右邊擺著一個玻璃櫥櫃,左方是大理石紋的櫃台,進門直走便是走道,走道右側則是更多承載童年的玻璃櫥櫃,四個圍成一個「口」字,裡頭多半裝著展示的玩具、模型,有的則空著,在玻璃櫃迷宮的後方,則是舅舅的工作桌,一台筆電靜置其上,一旁則是與紡織機合為一體的長桌,而兩側牆上,黑色的鐵網佈滿牆面,無數鐵鉤扣住網格、吊著玩具包裝,也勾拽我的目光。
小時候,我喜愛盯著門邊玻璃櫃裡的模型看,特別鍾愛一隻機械金剛的大模型,數層銀白的盔甲裝設在灰黑的皮膚基底,一雙深紅的眼睛雖有些懾人,然而,稍微黏歪的眉緩和了牠的殺氣,更重要的是,我親自組裝了這隻模型,儘管並非全部。
雜貨店內囤積不少模型玩具,舅舅遂讓我組裝幾盒賣不掉的模型,成品可以做展示用,我組裝的過程也能獲得不少樂趣。真要說做得工整、牢固的話,我想舅舅親自做肯定要比我好,舅舅的個性很拘謹,有時一絲不苟,聽母親說,他從前在日商工作時,還懂得繪製精密的工程圖,這種依照說明書就能組好的玩具,對舅舅而言,想必是輕而易舉,然而,舅舅更喜歡讓我拼裝這些模型。我碰到拼裝上的瓶頸時,往往動怒至極,而舅舅大概偏愛觀察我惱火地坐在工作桌前,生著悶氣、盯著說明書,卻又不肯放棄,現在回想,那時我生起氣來,也許散發著比平常可愛的一種固執,舅舅也因此而總是瞥向忙著找零件的我吧。
舅舅經常穿著簡約純白的短袖,天冷時則穿著長袖搭上深灰毛背心,從我有記憶以來便童山濯濯,戴著一副老式的金邊眼鏡,從母親與阿姨們的口中,舅舅與其外表一樣,是個嚴肅的人,然而,記憶中,滿滿都是他的笑靨,如今憶起那些畫面,舅舅倒像是一個小男孩,偶爾也會和我玩些幼稚的遊戲,結局都是我受騙上當,舅舅則笑得合不攏嘴。
除了逗弄外甥,舅舅還是有不少正經事要忙,像是繡學號,他的店除了販售上個世代的文具與玩具,還提供車繡學號的服務。繡學號講求心思縝密、專注,母親遂經常告誡我不要打擾工作時的舅舅,我卻不以為意,還是成天泡在一樓的雜貨店與舅舅聊天,舅舅竟也能一邊應付這個煩人的幼童、一邊在裁縫機前車好一件又一件的制服。
四處亂走之外,我也愛觀察舅舅繡衣服,一盞檯燈的照射下,舅舅的皺紋變得更多更深,像是時間在他臉上繡上了條碼,透漏著年齡的線索,而燈光所照之處,密集的藍色縫線,在被圓環壓住的薄布上組合出鏡像的文字。
後來,我鮮少打擾舅舅在雜貨店後方繡學號,我意識到這種縫紉的可怖,繡上去的錯誤,是修不好的。
小時候,我的臉頰很圓,於是,舅舅經常用客家話戲稱我「湯圓」,又恰好,我生氣時總是滿臉通紅,我猜我組裝模型受挫的時候,就像極了紅湯圓。
起初,我不排斥「湯圓」這個綽號,我喜歡吃湯圓,特別是紅的,幼時我渴望長大,巴不得每天吃一次湯圓,每天都長一歲。後來,「吃湯圓長一歲」變質成為詛咒,在大約要成長的年紀,我懼怕,時間會偷走僅屬童年的無憂無慮。
不過,若真要說「偷」的話,我才是可恥的小偷。
每次回外婆家,外婆往往給我零用錢,而我會用這些錢,向舅舅買玩具,多半是一些遊戲卡牌。
有次,舅舅難得引進新貨,我那時七歲,興奮得跳腳。
「粄圓!新版的遊戲王卡到囉!有更強的『青眼白龍』!」我剛走進雜貨店,舅舅就對著我喊。目光一轉,牆上還真的多掛了好幾盒全新的卡片,我看見包裝封面上、以閃光材質燙印的青眼白龍,興奮地大叫。我吵著要舅舅幫我把高掛牆上的卡盒拿下來,我必須瞧瞧它精緻的包裝,當然還有標價。當我看見標價,興奮的反應被按下暫停,空氣呈現一片尷尬的混濁。
我忘了新版的遊戲王卡比起前一版貴上多少,我也不想記得這筆贓款。倘若我等上兩個星期,兩倍的零用錢便足以馴服新的青眼白龍,舅舅的客人也多半是來送繡制服的,沒有人會搶光這些紙牌,但我就是不能等,我好衝動,衝動得令我懊悔。七歲的我,就為了一盒紙牌謀劃起一樁竊盜,不過粗糙得可笑。我走向門口的大理石櫃台,拉開抽屜,拿出數個拾圓,塞進口袋,快速轉身,手插口袋,頭也不回,急忙離去,然後,被逮個正著。
舅舅沒有責罵,只是要我把口袋裡的錢放回抽屜,我也沒有哭,至少軀體沒有,靈魂正哭泣著,哭訴著我的衝動可能偷走了更多,失竊的事物肯定不僅只是那幾個十元硬幣。那當下,愧疚是熱湯,淹沒我、燒燙我,而我,不夠格當那純淨潔白的湯圓。牆面上,密密麻麻用以放置掛鉤的深黑鐵網,頓時成為牢籠,我太邪惡,我盜竊了自己善良的一部分,我應該被押入真正的牢房。
繡上去的錯誤,是修不好的。
後來,我出於好奇去拉了那個大理石櫃台的抽屜。它是上鎖的。我親手於自己的良心繡上「小偷」二字,儘管舅舅貌似不在意,往後也未提及過此事,罪惡的縫線至今仍緊鎖心頭。
從此,學業是我逃避回到犯案現場的好理由,探訪外婆變得不再規律頻繁,如此便不用經常穿越雜貨店、不用面對舅舅、也不須面對自己,即便我經過雜貨店,而舅舅也在,我們多半只是招呼、寒暄,我總是立即走上樓梯到三樓的小房間,這不是我應該待的牢房,那裏有電視,而電磁波能暫時洗滌我的罪惡。舅舅後來便鮮少把囤積的模型交給我組裝、也不再叫我湯圓,而我還在逃避,把我與舅舅的疏離歸咎於時間的浸染,假裝我正在成長,而那些失去只是成長的代價。然而,儘管湯圓對於一個成長的少年聽來不很適切,拼裝模型卻不論幾歲都值得玩味,回首檢視,成長只是藉口,害怕成長更是誑言,對湯圓這樣食物的由愛生恨也與成長無關,頂多是一種逃避,逃避我遺留雜貨店裡的罪惡。
更令我像個罪犯的是,我在外婆離世後才意識到自己始終都在逃避。
隔年忌日,我十七歲,呆站在雜貨店內,看著裁縫桌上的數綑彩線、玻璃櫃裡的模型,才意識到自己的支離破碎,需要縫合、需要拼湊,外婆逝世後,我回來此處的機會只剩下祭拜或逢年過節,我不必再找理由逃避。
甚麼都變了,熱情奔放的男童不在了,外婆走了,唯一不變、也不會被偷走的,是曩昔存放在雜貨店的回憶。
【評語】
宇文正:
一樁「偷竊」事件,無法告別的罪惡感,成為童年的一記烙印。作者娓娓道來,對舅舅、雜貨店的刻畫,乃至「犯案」的經過,事後的逃避,細節豐富,無法追回的童年,令人惆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