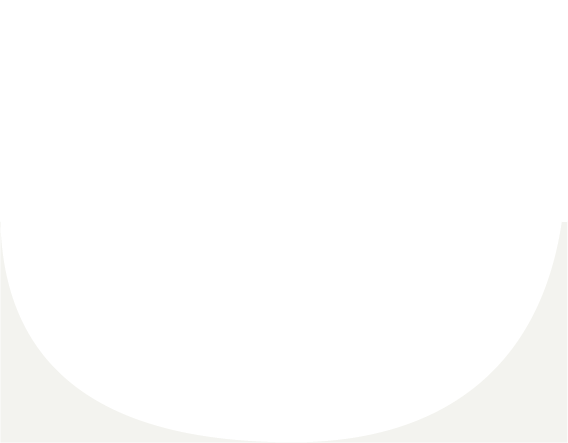works
文學獎專區
歷年資料

縫紉機
北一女中
帥佩妤
想和那台縫紉機的初識,是在我幼稚園,家人把奶奶從花蓮接上來的時候,雖然那已經是普遍的家電,就小小的一台擱在靠窗的木桌。奶奶是原住民,刺繡縫補的手工活似吃飯般容易,但也是顧慮她的年紀,願照顧我的閒暇別傷了手,剛搬進來沒多久,爸爸就把機器扛了回來。奶奶常嚷著浪費,說沒有必要,可眼裡正一閃一閃,微微流出了欣慰,她像個迫不及待見了新玩具的孩子,藏不住喜悅。
當時的新款,勝家牌的機種,光滑面的象牙白烤漆,「ㄈ」字的外型,奶奶笑是一個駝子,因為手腳不靈活才非用機器不可,才有了此般設計。上下有壓線、回針、調速度和針距的按鈕。誰沒有最皮的那段時間,在奶奶的半成品上一時興起,偷偷去胡亂按又調不回來,她回來一車便毀了整個花樣,挨一頓罵從來就不稀奇。木桌抽屜裡有一排針,前後也看了不下十幾次了吧,從來不覺得有什麼異同,有些套了橡皮,有些有霧面石黑的托,大多是亮銀色,魚鱗般的光亮,遠看一列排起來,跟之前跟奶奶去永安市場時看到的白帶魚有些類似,且在西曬時,末端都會有盤踞的一撮鵝黃色陽光。
奶奶的手粗糙而靈巧,有了縫紉機更顯輕鬆又別緻。吃飽飯睡意濃厚的午後,伴隨著規律的「扎、扎、扎……」,奶奶會一邊說故事一邊做活。依現在的審美觀,受民族色彩渲染過的圖案,這裡一顆珊瑚紅的石珠,那裡一朵大紫牡丹花繡,下邊又縫一個大理石光澤四孔鈕扣,「扎、扎、扎」地刺上布面。奶奶的小故事,伊索寓言也好,格林童話也罷,偶爾也教我她難得記著的幾句弟子規,也「扎、扎、扎」地繡上心頭。可能不小心說錯了小部分,可能哪條線沒走好,至少還是韌又實用的。
給針線來回綴過一次的童年,我也不信有了這一天。或許及早該發現,不論是輪廓扭曲的花瓣,還是日漸減少、奶奶自豪的作品數量。誰知道這樣一針一線,他們喬裝成皺紋,一來一回,蒙上她的雙手,她的雙頰,還結了鈕扣樣的厚繭。就是太多了,太遲了,連眼皮也給縫合起來了。而那些線料也不巧的是象牙白。
奶奶患了白內障。
那年暑假,午後只有乾澀刺耳又不規律的知了。
術後,我親眼見過那個傷口,那時的技術是植較硬的人工水晶體,會留下縫合的痕跡。那線一點兒也不好看,沒人喜歡,且術後叮嚀要保養眼睛,爸爸不再讓奶奶做裁縫,縫紉機被搬到衣櫃上頭,再也沒使用過。我又更恨那條線,它縫死了奶奶的樂趣,還有午後的故事。
上了小學,我又更自立了一點。升小二的暑假,奶奶回了花蓮,一是休養,二是想念姨婆和朋友們。家裡少了會裁縫的手,我也理所當然地沒了新布玩,沒了故事,也沒了奶奶。她的最後的半成品是個零錢包,正中間有隻用象牙白拋光面串珠繡了一半的雪納瑞犬。媽媽帶著去給市場那些婆婆,想至少把剩下的一半繡完,但就算是一樣的珠子,不同針式,不同
縫紉機,不同的人,不同的感覺,應是縫上去的黑色眼珠,我不喜歡,如同一顆不規則的珍珠,不被世人看好。
八、九年了,我為了家政作業把機子搬下來,這是從奶奶回花蓮後的第一次,給它插上電,我彷彿回到當初的興奮,眸子像迫不及待的孩子般放著光亮。可按下的第一針就對不上,一顆晶瑩剔透的珠子被碰到了地上,滾輪仍發出「扎、扎、扎」乾枯尖銳的聲響,它好久沒被熟悉的陽光擁抱了,厚重的埃灰和鏽蝕使它衰老。我彎下身子,拾起掉在桌角的那顆珠子,還有才剛落下,出自於我,透明又溫軟的另一顆。
【評語】
宇文正:
從縫紉機回想奶奶的手藝、午後的故事,結尾縫紉機生鏽了,從地上拾起一顆珠子,與想念的淚水相映。篇幅雖短,但精巧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