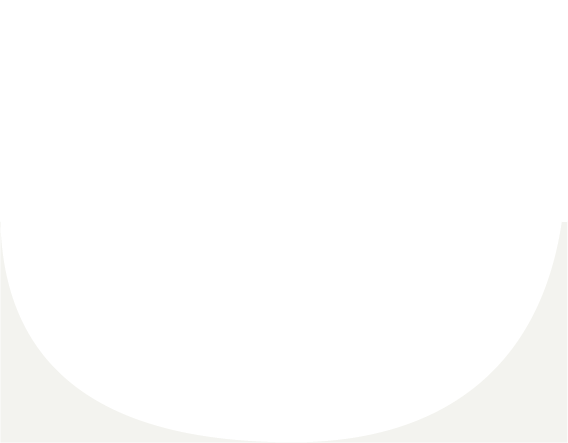works
文學獎專區
歷年資料

道是無情卻有晴
永豐高中
張哲維
我想,這會是段血淋淋的過程,將自己剖開、肢解、想辦法塞進狹窄的文字當中。但如果紀錄也可以是種追念,那我願意好好鐫刻下,這漫漫韶華遺留於我的所有。
最初的筆劃,是有些隨意的一撇,被寫在了五年前的陽光,斜斜的、悠長的,透過窗邊的玻璃灑落,餘暉熠熠,將男孩的輪廓柔焦成溫柔的光暈。逆著光,我不自覺慢放了他的回首,心被揪緊到讓人想哭,於是一切都來不及了。
對於青春期的少年而言,要察覺這件事其實很容易。不過就是一個有他陪在身旁的盛夏午後,你會驀然發現自己居然早已記住了,所有屬於他的即便最為瑣碎的習慣。儘管你想隱瞞,蟬鳴卻是聒噪得很,好似想拆穿誰的謊言,知了知了......
他不喜歡讀書,卻喜歡隨手翻弄書頁,有時候瞥過一兩句話,特別是被畫過註記的,就緊抓著向我問道為什麼。「欸,為什麼對年輕人而言,三年五載就可以是一生一世啊?」他手裡的《半生緣》被弄得啪搭作響,書籤落在了木桌上。我卻始終盯著他潔白的領口,第二顆釦子沒有扣好,他說過不喜歡被勒住的感覺。「因為年輕的時候,會覺得時間過得特別慢吧。」蟬聲突然被放得很響,知了知了。它們知了,這不是我心底真正的答案。「是喔」他漫不經心地應道。不久後鐘聲響起,我看著他走回自己的座位,時間開始變慢了。或許是因為我正等著下課,等他過來找我說說話,或是並肩走過被夕陽曬得暖融融的放學路。有時我會夢見那條路變得很長,如同一生一世那樣的長。
華夢總能實現一切,除了永遠。醒悟終究自夢境的穹頂劈下,像把寒光淒淒的屠刀,猛地一剁,路的中途於是被劋開一個血肉模糊的截面。從此人生被分成兩半,無論哪個卻都是慘死,半生無緣。
那是一堂健康教育課,投影布幕上播放著《斷背山》的片段。每當主角們稍微親近了些,四周的竊笑便也暗暗浮動,那時男孩子們的聲音正值變聲期,不成熟也十分刺耳。「他們這樣會不會得愛滋啊?」也忘了是誰這麼一句話,幽暗的教室頓時翻湧起歡謔的嘲弄,將我打落深不見底的大海,沉重的水壓好似
在捏破泡沫那樣,輕易地將一切化為幻滅。
我望向那個男孩,他果然笑得猖狂,然而更可悲的是,我也一樣。霎那間如同轟雷掣頂,原來這是段孽緣,上輩子虧欠那個男孩,沒還完,拖到這輩子來了。那年不過國三即將畢業,我卻覺得自己突然變得好老,眼茫茫的,看什麼都像是海市蜃樓。
「日子過得真快,尤其對於中年以後的人,十年八年都好像是指顧間的事。」
一晃眼,男孩的身影從眼前移到了手機上。通訊軟體顯示著他的頭貼,下方是通話時數的累計,已經持續了好幾個小時。畢業後我們考上不同的高中,聯繫依舊,甚至更加緊密,卻只維持不過兩年。
男孩打電話來除了閒聊和討論功課,更多的時候就只是擺著,我於是習慣了邊聽著雜音邊讀書,時而傳來咳嗽、打噴嚏、雜物的翻動……諸如此類的聲響,讓我有種依偎在他身旁的錯覺,也不知道是幸福抑或殘忍,猶如強忍著鏡子碎片扎滿手心的痛楚,也要觸摸一朵不存在於這世界上的,最美麗的花。
高二那年,婚姻平權的議題吵得火熱,把整個社會吵成了硝煙彌漫的戰場。
「男生跟男生結婚,真的是挺噁心的。」他嫌棄地說道,聲音聽著像是回到了國中時期。我平淡地應了聲,而後翻開《傾城之戀》的下一頁。書中的炮火無情砸落在白流蘇上方,這情節反覆看了好多遍,剛開始會心頭一緊,後來卻也逐漸習慣。「那種人應該是心理有病吧,女孩子多好啊,偏要跑去找男人。」他逕自說著,這次我沒有搭理他。柳原終於趕到了,用手托住白流蘇的頭,一邊急促的安撫著,柔情四溢,多好啊。
後來話題轉到成家立業,他說道以後錢賺夠了、對象有了,就會結婚。「男人就是該養家啊,你之前還說過不想結婚,不會是因為喜歡男生吧?」他笑得歡快,我也打趣地回應著,一邊用鉛筆畫下了註記——炸死了我,你的故事還長著呢!
那通電話之後,我就斷了跟男孩的聯繫。本以為孽債就這麼還完了,從那之後我卻時常失眠,闌珊深夜將它的顏色染進我的眼袋,還不斷絮絮叨叨著所謂漫長。每個無法入眠的夜晚,都像是佇立在一座繡蝕的大鐘前,楞楞地盯著那緩慢繞圓的指針,一圈又一圈,走在玻璃所反映出的人臉上,每輪轉一回,那張人臉就顯得越是憔悴,密密麻麻的血絲爬滿眼白,像是扭曲掙扎的血字,定睛一看,寫滿了「孽」。
想著會如同所有初戀故事的收場,由似水流年拉下舞台的帷幕,它卻只是匆匆淙淙地流過,潵後沒了執著,徒留麻木,一種失去所有感覺的感覺。人們會在那樣的麻木當中學會成長,為了得以從容訣別的那天。
實在是太過平凡的一個日子,平凡得好似能從窗邊的日曆抓下同樣的一大把。通知鈴聲選擇了在這樣的天,倏地自手機彈起,清脆得有些曖昧,像是故作淡定卻弄巧成拙的模樣。一句好久不見,在通訊軟體中顯得更加雲淡風輕,還問道週末要不要碰面。我思索了整整一天,不是想著該不該赴約,而是該如何為這段孽緣劃下句點。我有想過對他撒盡這五年分的羅愁綺恨,可是那樣顯得太過小家子氣;也想過索性已讀不回,可又覺得太過草率。拿捏不定之下,訊息就這麼被擱到了睡前。
那陣子的雨總是下個不停,加上歲時漸漸入冬,躲在暖暖的被窩裡聽著冷雨敲打屋簷,有種舒適的安全感,滴滴答答滴滴答,「改天吧」,這三個字被飛快地輸入後旋即傳出。蟬鳴這次沒有響起,它們的羽翼早已化作塵埃,失去了聒噪的理由。隨後只覺得心情如釋重負,像是走了好久好久,才終於到達旅程的盡頭,我會在那愜意的坐下,靜靜目送男孩走遠。
願炘炘暮曦將你的前途灼曜得煒燁,唯獨留給我一剪背影,作為僅有的眷戀。過去我們總是並肩走著,所以這將會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眺望你的背影,直到你頭也不回地,走出了我的視界。最後的光陰總是沉默,多麼靜謐,多適合下葬過去的自己,連同這段孽緣,輕輕覆上時間的荒土。
然而我還有下輩子要過呢,輪迴不過是將該帶走的帶走,該留下的,來日歲月終究漫長。簾外雨潺潺,我卻如此肯定,明早醒來,世界將被洗滌得煥然一新,地上的水漥會盛滿雨過天晴的碧藍,有多少傷疤,就倒映多少驕陽。
【評語】
鍾文音:
作者才華細緻,感情刻劃頗有文字功力,唯也因此常常文字超越了情感,形成一幅彷彿停滯的內在風景。藉著閱讀勾出背後的所思,將張愛玲《傾城之戀》與白先勇《孽子》藉著時間流動而能彼此互文呼應,呈現高度的曖昧流動,讓我想到荒人手記式的異色之情,在荒蕪之上長滿傷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