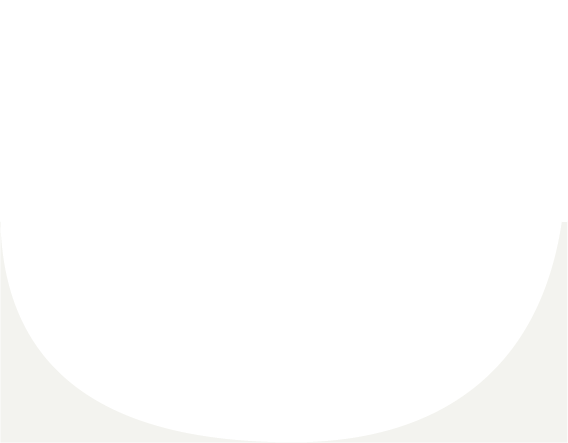works
文學獎專區
歷年資料

間歇性失語
南山高中
曾子薰
阿妙不是臺灣人而是緬甸人,前幾年獨自一人來到臺灣。眾人覺得她人生地不熟語言不通,講起中文來結結巴巴,大部分時候人們都聽不太懂她說的話,幾次溝通不順下來她便不說了。阿妙有時能說,有時卻一個音節也發不出來,是為新住民獨有的間歇性失語症。
剛開始,阿妙不說,是因為不會說。
初來臺灣時她才十八歲,在她的家鄉看來已經不太算是年輕漂亮的年紀,到雇主家,奶奶卻道她是個妙齡女子,喚她「阿妙」,從此她在臺灣有了名字,而原來的名字倒是沒什麼人想起。
臺灣外文潮盛行,阿妙也說外文,可她的語言似乎很少人學,雇主家沒有人聽得懂緬甸文,她只好硬著頭皮說著兒時不認真學的英文,幸好她雇主的英文說得跟她一樣支離破碎,不幸的是,她跟他們的連結又少了一些。
阿妙英文不好,現在她要學著說更難的中文。她在廚房裡偷聽一家人在餐桌上的對話,模模糊糊拼湊出一絲頭緒。說「好吃」時,每個人臉上都洋溢著歡喜,阿妙想,或許這是表示高興的意思。
第一次收到薪水時,她笑著跟雇主說:「好吃好吃!」大家都笑翻了,阿妙也跟著笑,臉卻悄悄脹紅了。之後阿妙就很少說了,大概是因為自覺了解得不分明,更可能是因為她又擔心被笑。
事情大概過了四個月,她跟幾個鄰居家的移工姊妹湊錢結伴去學了中文。
開始學中文後,阿妙知道「好吃」是肯定食物的話,她又不好意思起來。她還記得有一天課程教到「妙」,妙是女添上一個少,是為少女,少女是年輕女子的意思。阿妙便想,自己原來還算是少女嗎?「少女」是一件好事嗎?
奶奶總跟她說,妳這麼一個年輕的女孩子,一個人離鄉背井,長得漂漂亮亮、標緻得緊,但能燒得一手好菜、洗衣打掃盡數包辦,不埋怨不生氣,絲毫不像現在那些脾氣潑辣、性子不溫順的臺灣姑娘,很讓她感到放心。阿妙卻不知道這是否就是「妙」該成為的樣子,在異鄉的土地上,她應該是什麼樣子的人呢?
本來阿妙是不太念書的。在緬甸的日子她每天煩惱家裡的生計問題,她是長姐,家裡有五個蹦蹦跳跳不得消停的弟弟妹妹,她沒心情也沒心思去在意那些文字和數字拼湊出的知識。
平時放學後的時間就去收附近人家髒了的衣服回來洗,有時洗一堆下來,手都起皺破皮,露出底下的粉紅。阿妙時常痛得不敢把手泡進混雜洗潔劑的水盆,可她是家裡最大的孩子,始終覺得自己年紀不小,應該扛起一個家庭的擔子了,好像洗著洗著,就能給家人洗出好多新衣服出來,可惜洗衣換得的錢連湊得一週溫飽都顯得困難,穿著沒有補丁的衣服也終究只是她搓起泡泡水時的幻想而已。
臺灣的雇主給的待遇算是挺好,讓她不愁在臺灣的吃穿,也有足夠的力量養活逐漸長大的弟弟妹妹,剩下的錢,她能用來做曾經來不及做的事,學的卻跟以前的八竿仔打不著,總覺得始終無法跟心裡的聲音產生共鳴。
阿妙感覺這個社會好像不太喜歡她能言善道。臺灣是個四面環海的國家,好多訊息來自四面八方,進入她的世界,在四下無人時暗自萌發,可是她不能說,不能評論政治、女權,人們希望她聽懂他們的想法跟要求,但並不怎麼希望她表達意見。她聰明而能發現這個社會的悲哀:她是外來的,她不該對陌生的地方品頭論足。
有天她心血來潮算了算,發現她來臺灣已經有五年左右。二十三歲了。儘管一段時間下來,她已經能說出自己想說的話,可她好像一說出來就要嚇到人,「阿妙?妳在說什麼東西?」似乎會聽到旁人的驚呼,似乎會被審視的目光指指點點──太機靈的外來移工恐怕不符合臺灣社會的期待,因為國家不對、母語不對、膚色不對,她並非知識廣博的高等移民。
她的雇主期望她乖順、聽話,要夠敏銳但不能太聰明。這世界上怎麼會有這麼矛盾的人呢?他們對她很好,卻不是對真正的她的好,「阿妙」有著第三人稱的性質,具有不主觀的無個性,是被所有人一起塑造出的龍套角色,她終究不是獨一無二的她,沒有過去那些經歷,渾然天成像是她天生就是個做家事的天才。她真的很好奇,什麼時候會有人注意到她粗糙的掌心,而不是她多能幹、長得多好看?
她好想成為奶奶口中的臺灣姑娘,那些情緒化的細節有著鮮明的個性,只是她不知道,是否臺灣姑娘在社會上好多角落努力爭取的那些本應平等的權利也能通用在她身上?可惜她連表現自己都不行,若是如此,她會害那些潛藏在社會下的古老的偏見下不了台,只能讓刻板印象指著她的鼻頭罵:「只是又老又窮的國家過來的人能有什麼想法妳也不過一個外勞而已還以為自己有多了不起。」
結果學了中文,最後也只是在老師跟其他移工朋友面前練習著說而已,像是一種消遣。其實她能說得很標準了,然而在人前她依舊說著一口生疏的中文,帶著奇怪的腔調,好像不這麼說反而不像個所謂「貧窮國家的勞工」。究竟刻板印象是她本身,還是刻板印象成為了她這個人的框架?
人盡皆知,阿妙起先不說,是因為不會說,卻有誰想得到,如今阿妙不說,是因為人們不希望她說。
儘管學會中文,但她依舊說得不多,說得小心翼翼,會說卻不能直說,想說可是不能說得太多。要自發性患上僅好發於本地人眼前的間歇性失語症,是她在成年後的五年學到的人生哲學。
於是阿妙就這麼成為──模樣好使喚但不甚精明,沒念過什麼書,看起來不太有主見,就像雇主、奶奶、鄰居們以及普羅大眾認為她該成為的樣子──臉譜化的異國色彩、臺灣一角不起眼的存在了。
【評語】
宇文正:
從語言的掌握,探究移工女孩阿妙試圖融入這個社會面對的問題、處境,語言象徵著阿妙的自我認知,以及外人的期待值。探索的角度別出心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