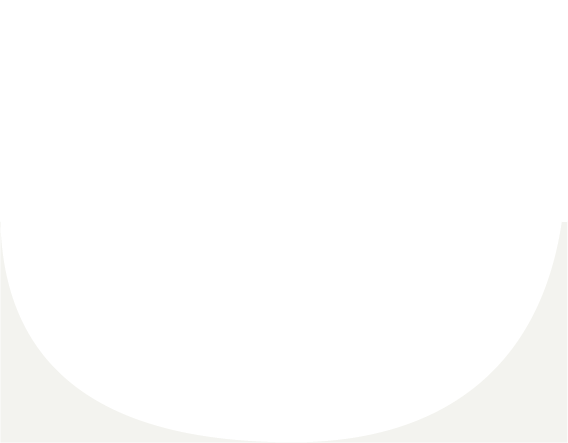works
文學獎專區
歷年資料

時間之磨
北一女中
游涵宇
時間的滾輪總是無情地壓軋,直到所有人都粉身碎骨。你呢喃著說。
你從來是個幸運兒你,是讀書和測驗組成的緻密篩網上滑順通過的麵粉粒。仍記得那個八月的最後一天,那個溫暖的清晨。承著夏季末期的微弱氣流,你踏上寫著「往綠洲」的首班公車,往重慶南路奔馳,途中經過被捷運黑暗期壓迫而狹窄粘黏的南海路。當時你視之為置身桃花源前的石頭裂隙,而你正要長出神所賜予的翅膀。但在顛簸的路上,公車晃著便穿越了蟲洞,轉瞬間四個季節都過去。你這才發現自己已經站在沙漠中央,看著褪色的制服,那些發光的想像正和年久失修的天使石膏像一樣逐漸斑駁剝落。
上帝為你開了一扇門,房間的其他角落便注定陰冷。一段腐敗發臭的感情、一團打了死結的人際關係和一個扭曲變形的研究架構足夠用歸納法無情地證明。
你熟記著已然渺遠的那個晚上,他戴著單邊的藍芽耳機和你通話,假扮成計程車司機,「我想載你去快樂的地方啊。」他半夢半醒地說著。你壓低聲量回答,「那就不用開車了。」就在這裡,不要再走了,你在心裡吶喊著。可是他義無反顧地開往睡眠,沒有留戀地開往你再也抓不住的遠方,徒留你反覆播放這段陳舊的錄影帶,拼命想證明這裡確實留下些什麼,但無人接聽的電話宣告他永遠成了失蹤人口。
天亮後到了教室,所有的應對進退看似和諧,無法解釋的沉悶氛圍卻綿密地交纏在你雜沓的心思上,勒得幾乎要出血。直到放學後漸入黃昏,三五人之間的細軟耳語如同包著布的鈍器,聲波穿越冰冷的空氣,厚實地打在身上,一陣熱辣。妒忌、觸怒、打壓、侵犯……,話題伴隨著不堪的詞彙包裹在笑語之中,和白天的秩序僅僅只有幾分鐘之隔,卻像是到了世界的顛倒面。英文片語裡綠色總是代表著嫉妒,而此刻這樣醜惡的顏色正被你牢牢穿在身上。你轉身奔向校門,逃離紛擾不歇的綠洲,嘗試埋首研究以轉移注意力。
然而往返於學校和實驗室的公車穿越冗長枯燥的羅斯福路,沿途的景色被框限在高樓和方形的窗,成了阻擋視線的粗硬鐵絲網,消磨了精準和理性之外的所有思路。「難道這不能像考試一樣有標準解嗎?」分手的兩個月後,得知班上氣氛為什麼詭異的同一周,實驗迎來了毫不意外的第十次死胡同。你成了鬼魂,執拗地固守自己學業上的順遂,不願面對早已腐朽崩塌的生活。「凡事總有第一次。」實驗室裡還迴盪著玻璃破碎的聲音,已近中年的器材管理員輕聲地說著,儼然一個經驗豐富的先鋒。你止不住的哭泣,好似墜落的是搪瓷娃娃。最痛的往往是第一次。
曾經意氣風發的初生之犢,如今變成困在專題研究和能力競賽的輪迴裡,被強迫推動石磨的老邁牛隻。你畏懼那些失敗的陰影會鎖鏈一樣地纏住你,帶你在時間的洪流中沉沒,所以推開了玻璃碎片,壓住了手上滲血的孔洞後,讀教人如何正向思考的書,諸如「相信自己」、「適時鼓勵」或是看來十分諷刺的「面對挫折」,奮力假裝所有事情仍在掌控之中,自己仍保有過去的榮耀。每天和不同的面孔爭論著知識的正確性,或威逼或惱怒地使人信服於你,像邁入衰老的帝國空虛地膨脹自己。
「這種生物在生物鏈的意義是什麼?」在一個自我介紹的場合,當你第二十次說明自己
的研究,說著實驗室裡那透明似蚯蚓的生物,那張陌生的臉問。「生物不需要有意義。」你害怕被質疑自己的研究實則是一無是處的漿糊,所以說,「牠能活下去,這件事本身就是意義。」最後你們以這是哲學問題為由驕傲地打斷,可那濕冷的戰慄感從此爬上你的背脊,猶如一隻隻蚯蚓。失序的正向思考終於領著你一頭撞向山壁。
「我所堅持的『我』有意義嗎?」從此你開始克制不住地想,思緒摔落谷底。
你逃避面對夜晚的到來,連光都遠離你的時候行動就無法控制地凝滯,變得緩慢,而這讓你有了自己是失能者的自卑;你不願和自己獨處,於是拚命求人認同,把自己活成了以評量和分數作為特技的馬戲團;你不曾真正認清自己是會犯錯的普通人,彷若中世紀教會偏執地堅持地心說,掙扎著想做荒謬的困獸之鬥。夢裡反覆上演的不再是童年時關於未來的彩色想像,卻常是舊時黑白電視中的奇異畫面,你在裡頭總是赤身裸體踩在沙漠上,卻尋不著遮蔽物,恥辱感腳印一般如影隨形,拖曳成無限延伸的疤痕。
而一切起因於你所堅持的「我」的意象。
自幼以來失敗於你是光年以外的存在,你追逐著紙上的數字和獎狀上的名次而活,當時相信自己握住了所有,卻在這些「成功」逐漸積累的同時被它所綁架。堆砌出「你」的元素是如此單調,一如物種單一化的生態系瀕臨崩潰。童話中那隻杜鵑用自己的鮮血染紅一朵玫瑰,你將自己釘在讀書考試的十字架上,魂魄化作那些生冷的數字卻毫無後悔,而那些恰好是石磨的齒,即使沒有鞭子,仍夠逼使你這已被摧殘得羸弱的驢朝前方走去,被奴役著直至終老,卻以為是自己推動了人生,跟聊齋誌異中執迷不悟的腐儒並無不同,而且還像座地基不穩的金字塔,只需要幾個稍顯尖銳的挫折便足以擊碎你自我形象的泡影。
你還是每天搭著公車往綠洲。縱使你晃得作嘔,公車依然每天準時接送,稱職的司機不帶感情,正確無誤地駛著,彷彿他開的不是車,而是流動的時間,你的時間就在這沙漠的中央緩緩消磨,而你身上的綠色制服服貼安穩,無辜地依偎著你。所有事物不對你帶有任何一點惡意,甚至也沒有情感,只是你在停滯不前的時候迷失了方向。
你才忽然明白,時間的磨不曾傷害過你,束縛你的綠洲從來都是海市蜃樓,牽絆你往前的唯有面對自己本質時的恐懼,以及構築幻像時表露無遺的懦弱。遑論那些如業火焚燒的第一次,不過是過度害怕失敗、近似於處女情結的病態所導致。根深柢固的倔強使你不願割除身上癌細胞般嗜血的自傲,拒絕承認自己的失敗,彆扭地選擇閉上眼睛,在荊棘滿布的叢林裡衝撞,竟還妄想著能有一條生路。也許你是該明白了。
你終究會是遍體鱗傷的獸,在殘酷的荒漠裡逐漸枯萎,你希望時間的風會將你化為塵土帶走,但無論如何解構自己,那些來自荒蕪的回憶都如影隨形,除非你願意睜開眼睛,不再欺騙。你緊緊抱自己,終於找回放聲痛哭的能力。滿是理想地在名為世界的玻璃瓶裡衝撞必然惹來一身傷,但你不再恨,童年形塑出的「你」已然定型,但你嘗試坦誠以對。時間的磨從來不曾追趕,或是輾壓任何人,它只是堅定地往前推移,把每個人都壓實成自我的立方體。
公車又駕著它沉重的輪子駛來,只是這次無論搖晃顛簸轉彎急煞嘔吐暈眩,你試著站直身子。
【評語】
鍾文音:
文字靈動,敘述自然,將上學的這條羅斯福路公車的情思流動筆尖,成了鬼魂的你,冷眼看著時間將稜角磨出了傷痕與圓融,斑駁剝落那說不出口的成功背後的荊棘碰撞,緩慢體
現著堅持的意義,企圖從高壓的圍牆昂揚自我心志,是一篇隱藏的明志文,結尾很有力量:你試著站直身子,意象飽滿,勾勒一場自我對抗與殘酷現實的青春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