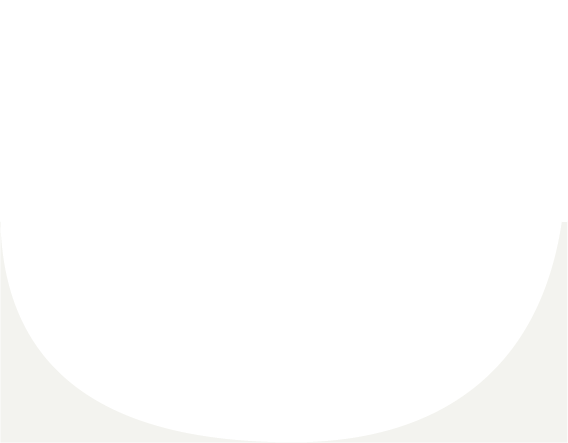works
文學獎專區
歷年資料

疼痛整復師
國立彰化女子高級中學
黃季琁
疼痛整復師
人的身體是張地圖,與生俱來,細密而繁複,臟器、穴道、四肢,該在哪就在哪,各安其處;而性狀,比如眼皮單雙、鼻樑塌挺等具不同樣態的特徵,在最初最初的一刻就被擬好藍圖,等到長成對自己足夠了解的那一天,得以恍然大悟的定位經緯,歸類自己哪些像媽媽、哪些像爸爸,坐標般明確。
我,也是過了很久很久,才驚詫地發現這件事。
簡單的診所、兩張推拿床、被疼痛坐滿的等候區,每天有大票的人拖著鈍化的身體,來了又去去了又來,嘴裡咕噥五十肩或網球肘病情云云。叩上門的都是痛,而爸永遠只是笑笑,像在笑他們一向擅長庸人自擾。
或臥或趴,患者遵循爸的指示,如一枚小兵唯命是從、不敢妄動。手肘陷落穴道,二十年來精準如一日,爸清楚知道,那些關於身體裡的結該如何解開。
伴我多年的疼痛,也只有這雙手有治癒的能力。
疼痛源自於六歲。嬌氣如我,尚且拿捏不好軟磨硬泡和無理取鬧。應該只是些芝麻綠豆般的小事,也忘了,六歲的本領不就是為了爭一個順心如意也甘願鳴鏑擂鼓嗎?一切叫人不耐。
回憶裡,我哭得滿臉通紅,倒抽鼻涕與換氣的聲音灌滿全身,爸激動的不停咆哮著些什麼,最清楚的一句是他不要教不會的小孩。我以為我就要被遺棄,那愛哭濕黏的體質又更加起勁。連不要哭也學不會,爸從來不是耐心的人,手提起,再落下,我與他便崩陷成墟。
收復寧靜,我發現我虛脫的撐在牆邊,肌肉是抖瑟後的肌肉。我好小,在爸的掌下若有似無。臀部那一灘稀淡紅色發熱的狠心,我剎時困疑起爸究竟是處理痛的人?還是製造痛的人?
不能理解。在那如雷的巨響擊落後,對爸的恐懼像在某一瞬間闖入我的血肉並緊緊相嵌;而恐懼又如同帶有與爸磁性相反的攝石,不斷的、無窮遠的排開我們。
從而形成裂谷地帶,一道關係上的痕。
溝槽流淌畏怕,所以僅能帶著泛紅的臀部長大。悄悄學會在任何日記作文避開有關父親的話題、刻意在他深夜歸家時熄燈當個裝睡的人、簡扼的使彼此談話扣緊下一期補習班收費袋的數字。能不親近就不親近,我說服自己這不是偏激,是無助的不曉得如何揮別父親的凶悍。
這實是關乎親子間的問題。那本該向父親撒嬌賣甜的幾年,恆常僵硬生澀,憋起畏懼我只當成唯唯諾諾的小貓,生怕做錯什麼事又將回到從前那無盡的夢魘。痛與爸本是兩條平行線,然而誰也沒料到六歲那樣一痛就是深入骨髓,所謂理想的父女也全都糊里糊塗的賠進去。
有解藥的,但我從不尋覓,只是自顧自相信自己忘掉的能力。
而後慢慢走到會因外表而起伏情緒的年紀,那些煩躁的日子像掉進濃稠而凝滯的流體,無時無刻皆戰戰兢兢的放大檢視身上不甚滿意的部位,陷入一個又一個挑三揀四的迴圈。
那全然悖離心願的煩悶,淺淺齧在體膚上,點滴刺痛,卻星火燎原。
青春期以後,我特別厭惡照鏡子。那是一段潛聲卻輕易決定未來幾十年長相的時間,在刻意觀察之下,我的身體好像絕對原創、又好像依稀可見模版。
肌理膚觸深刻的令人發疼,但我更不希望爸為了工作以外的事情煩惱。也
不習慣他對我投以過多關心。
爸察覺我總習慣在浴室鏡前矗立許久,彷彿才意識到我已經很不一樣。而他只是在我那樣重複嫌棄自己的日子裡,輕皺眉頭說:「青春痘不要擠,女孩子留疤不好看。」他在意的是疤,爸對所有的疼痛衍伸物都過分敏銳。
可他從未看見困在我們之間的溝壑,我和他的患者始終不同。
爸微微俯身,像一株挺拔的榕樹,氣生根蔓延每個有痛的內裡;長方形的推拿床他來回走動,眼睛有光閃爍。我想起這些畫面,也想起已經不去診所很久了,久到記不清那裡的海風是怎麼樣的鹹,可耳畔仍然常在是清脆的骨頭喀啦喀啦聲響,像海浪敲擊空氣,也像一堆乾柴燒的很烈。
爸的手粗糙厚實,貼著患者的穴道就像與之共同吐納,壓進身的每一下都帶有目的,並且永遠精準。
在我許多年沒去診所後,一個沒有星星的夜晚爸拎回一包中藥,要我按時吃,調身體、降火氣、這樣青春痘才不會再冒;而往後好多個墨水般的夜深人靜,祛疤藥膏、養顏秘方、皮膚科名片皆如月光被刻意挾帶進屋,這全讓我更不懂爸,他從來不需廣泛嘗試、也不必賭哪個有用,但他卻一直一直這麼為我做。
明明知道青春期就是青春期,不管是痛是傷是疤,什麼都由不得一點入穴。
那些終究徒勞。我的手指依舊如焦躁的蛇在爬,爬在青春痘鋪成的顛簸碎石子小徑。我生的從不理想,被迫帶著所有屬於我的繼續成長。有時候並不喜歡身體這麼實質的事物,那其中盛裝著太多與自己願違的無可奈何。
我花了滿長一段時間去適應自己的外貌與形體,後來終於連同青春痘一起,稍微放過不像山峰的眉、不像汪洋的眼,以及其他好多好多。
於是青春痘持續故我,我流浪在清晰的羅盤。
過了很久,一個寒冬天,爸帶我去他最喜歡的火鍋店,外頭風颳的刺,我把自己包裹嚴實,密不透風很好。我點咖哩、巴望爸鍋中的麻辣鴨血,熱呼呼的氣飄散在我們之間,此刻有什麼值得卸下。
爸突然認真地看著我:「哎!妳的青春痘真的和我年輕的時候一樣。」我神色一愣,為了接話而笑了笑說:「沒有辦法,青春期啊!」
我用力迴避著,諸如「和我」、「一樣」等強烈字眼。
啵啵啵,火鍋滾的熱烈。「要不要?給妳。」來不及反應,兩塊軟嫩的鴨血老派地滑落我的碗中,心裡也像是被什麼給入侵。我抬起頭來,蒸氣卻已像場大霧隔開兩人,透明又迷幻,隱約間我僅見著他的五官—濃眉、單眼皮、生過青春痘的皮膚,我與他的軀殼在那時刻重疊、分離、重疊,那麼契合,那麼神離。咬一口鴨血竟嗆辣得咳嗽起來。
爸只是希望我不要像他、女孩子不要留疤。十幾歲與六歲的,都一樣。
無形之間我竟仍不偏不倚地長成了他。
我終究是驚詫地發現了,澈悟之前,山川河水崩落—我像爸爸。我的坐標坐落在他的坐標,悶騷是、特徵是、疼痛也是。我和爸如此近如此遠,在我逃避他的時候,我的身體不曾換骨,如如實實的該怎樣就怎樣。
我還是沒有走向爸,我也弄不清楚我在等什麼,難為情的說有點彆扭,哪柔軟的說親近就親近。
父女痛,我為之命名。我想爸一定不會介意任何形式的疼痛,只不過是我混淆職業與人父的異同。
推拿是把破碎的山脈縫合、把支離的川水接泊。爸永遠在,也永遠懂得治癒的方法—揉著按著使一切恰到好處、慢慢平復如故。
傷是用來結痂的。
人的身體就是張地圖,我像爸,因痛而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