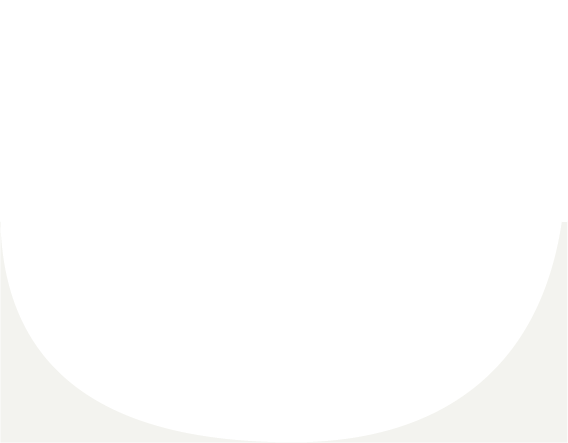works
文學獎專區
歷年資料

澄澈
國立新營高中
簡宏頴
澄澈
澄淨無雜質,品質保證─至少瓶身標語是這麼寫的。
拖著沉重的步伐從床邊走到浴室,鏡子裡映射出一個憔悴疲憊的面容,眼皮像鬆了螺絲的鐵捲門,上上下下不停刮出刺耳的聲響。每日早晨都像這樣逼視自己,口中唸唸有詞地重複昨天背到一半的英文單字,破碎的音節間少了好幾個字母,和那裂成玻璃脆片的睡眠夜晚一樣,永遠得不到滿足。
常常感嘆這樣苦悶的高三生活何時結束,水藍色的制服繡著發黃霉塊,被墨綠色的側背包壓得發皺,清流都成了一池汙水。美術老師說互補色可以帶來視覺張力,我想應該是繁榮和枯萎的對比吧:不是在其中一方載浮載沉,就是在另一頭垂死掙扎,彷彿太極的二元分界,切劃出毫無詮釋空間的冰冷界線。
收拾好書本,踏出黏膩的步伐到學校。日子還不是這樣一天天的過,為了養出肥美的榜單鵝肝醬,將玉米和大豆灌入鬆弛疲乏的胃袋,撐成飽脹欲裂的鼓囊。結束辛勤進食的一天,任務還沒結束,要到每天必經的雜貨店,一邊和老闆娘談笑風生,一邊把一支支透明的瓶裝液體塞入背包。如果「走私商」也是一種工作的話,那我也算精通戰技的老手了。
倒也不是為了料理或祭拜,那些米酒都是要拿來喝的。
摸入光線暗淡的房間,還要留心腳步以免被散亂的雜物絆倒,紙箱空瓶衣架或內衣或襪子,明明只是不到幾坪大的小房間,竟像一個錯綜複雜的迷宮。越過重重障礙,才能觸及那個坐在床頭纖瘦的身影,
我的母親。
接過一瓶晶瑩的酒,熟稔的開蓋動作不帶一絲猶豫,然後仰頭一灌。彷彿喉頭有隻飢渴的獸,出於本能而肆意撕咬吞噬,像用印度的恆河澆灌非洲的荒土,但歷經一陣濕潤滋養過後,隨之而來是更多的乾燥與燒灼。三分鐘的歡愉換來三天的宿醉,試圖把憂思暫時盪出玻璃窗外,再被強制拉回房間,然後無限循環。
忘了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我們家就這樣碎裂了。也許一開始只是小小的細縫,容不下一絲憂慮與警覺,後來細縫逐漸擴大,如孢子蔓延開來而盤根錯節。現在平滑的表面已經裂出一道谷隙,足以滲入幾公克的謊言與仇恨,隨著藥量加重而融化於每聲爭吵的怒吼之中。離開書聲琅琅的教室,回到家中又是另一番唇舌交戰。
承受著挨罵受打的風險,我還是那麼做了。明明知道自己不該給母親送酒,每當面對面時,自以為堅強的心靈堡壘卻往往動搖,直到土石崩毀。似絕望似哀求的幽光從她釀成漆黑的雙眸漫出,像做錯事的孩子祈求獲得原諒,能獲得赦免再享有另一次犯錯的機會。
我太想得到母親的認可了,只因她是我最親最愛的人。還記得小時候她牽著我慢慢走到雜貨店買糖果餅乾,甜膩的氣息瞬間瀰漫空中,那是草莓味或柳橙味的夢,但到現在卻只剩下一股酒精的辛辣感。傷口正緩慢燒灼著,像實驗室的酒精燈,一種詭異的平衡狀態,在燒杯中等待沸騰純化的,是母親混濁的靈魂。
杯中溫度一點一點攀升,也許再多加一點壓力就會變成超臨界流體,或能萃取出一點透亮的結晶。但事實證明這不過是墮落的煉金術,而原料是十七年不圓滿的家庭生活與積累的債務均勻混和,並在憂鬱症的催化下靜靜發酵。
於是,一場無聲的交易就這樣達成協議。
我滿足她生理的渴望,而她補足我心靈的空缺,像一個殘破的天平,窮盡所有努力來維持一個不穩的平衡。長大後再也沒有機會牽起的掌心,只能透過遞酒瓶時輕微的碰觸指尖,來感受記憶中的溫存:一幀由掌紋編製而成的地圖。當然我不會忘記,纖細柔弱的指節早就因慢性酒精中毒而發黑、僵滯。
強烈的罪惡感不斷侵蝕著我,卻令人難以自拔,我知道這是錯誤的事,卻是能讓我得到親情之愛的唯一方式。雖然選擇在她面前當一隻溫順的綿羊,但內心有股微弱的叮囑輕聲迴盪,殘存的理智與良心告誡我,不能讓自己就此沉淪。
上一代的失敗與錯誤,不該被複印到下一代,也沒有傳承的必要。
最近我常騎單車到阿里山散心,藉此釋放平日積累的狂暴與憤恨。貪婪攫取山林蓊鬱的枝葉,試以杉木紅檜重建一個心靈的居所;瘋若猛獸地吞飲山泉水,試圖稀釋心中的酒精含量。我開始借助自然之母的慈悲來療癒內心,拖著殘破不堪的身軀,想要撫平那些曾經滲血的傷痕,尋求一點慰藉。
但願我能將山間的清風吹入母親的內心,用冷泉洗去她心頭纏結的憂思;但願我能擁有太陽的光輝,把一絲光芒透射進她陰鬱黑暗的心;但願我能長出結實的臂膀,重新將她從深淵拉回。我知道外公也有酗酒的習慣,所以母親或許也經歷了我的苦痛,但我和母親不一樣,我想成為改變的那個人,想成為掙脫韁繩的那個人。
不會忘記那些一同漫步的日子:陽光自樹葉的間隙流瀉下來,照亮紮實的紅磚道,輕輕牽著溫暖厚實的手掌,走向熟悉的雜貨店;或是在廚房中大顯身手,一同把鍋碗瓢盆敲得響亮,與排油煙機轟隆的運轉聲對喊出一道道五顏六色的菜餚。陳舊的記憶如泛黃的相機膠捲在腦中回放,彷彿時間回到十七年前風和日麗的那一天。
那時河水都是澄澈的,也沒有一池一畔受到汙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