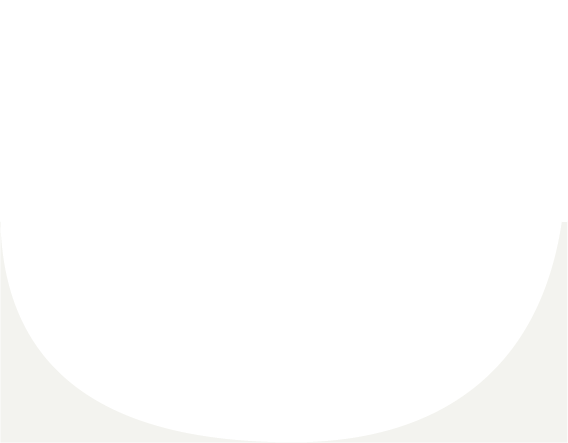works
文學獎專區
歷年資料

赤腹鷹南飛
國立臺東女子高級中學
林毓恩
當一群赤腹鷹由渺遠的雲中如潮水湧出,我感到一陣心碎。
昨夜長達七小時的夜間蛙類調查讓我晚歸,欲就寢時已過子夜,今早六點四十又被生理時鐘喚醒。我拖著自己走在四格山木棧道階梯上,部分木板因潮濕而腐朽,沒吃早餐的身體像是在風中站立過久找不到熱氣流的大冠鷲,翅膀舒展得十分辛苦。
從入口走到山頂涼亭用不上五分鐘,到達前一、兩個小時已有三位鳥友在此等待,分別是大衛、埃圖以及埃圖的爸爸。在初秋猛禽過境南遷的時刻,鳥友的精神與寄託幾乎棲息於此,直到鷹群裡最後一隻灰面鵟鷹離秋季而去才稍稍依歸。瞥見大衛揣著相機坐在涼亭旁欄杆上,我邊喝水邊鬧他不是說今天爬不起來,又說起昨夜共同目睹的百步蛇。埃圖原先坐在欄杆另一頭,見到我,幽幽地打了個招呼便走向無遮陰的平台。聽他口氣,毫無疑問,我一定是錯過了好幾場起鷹。
同樣都是秋季的過境鳥,與十月到來的灰面鵟鷹相比,赤腹鷹體型較小,飛行上也更仰賴熱氣流輔助以節省體力,早晨牠們藉熱氣流盤旋上升至高處,高到能看見山的靈魂時就會跟隨風勢力道滑翔,完成一場完美的起鷹。集結成群的赤腹鷹盤旋繞轉,形成一個完美的黑色大漩渦,列隊離去時則會成為一條似乎沒有源頭盡頭的大河,從漩渦到大河,不管是誰,人們初見此景的瞬間將同時感到震撼與錯愕。
我拿著Nikon的初階望遠鏡(買下它的那年耗盡了我所有的零用錢)走到埃圖身旁
08:01,涼亭東邊出現二十六隻赤腹鷹,我想是起鷹吧也許不是。08:10,赤腹五隻。08:13,赤腹四十五、蜂鷹一。08:21,赤腹十一。08:30,赤腹十,來了兩隻大冠。漸漸,埃圖的爸爸依然細細觀望平台以北的群山與雲層,我們離開涼亭陰影下的次數卻減少了。兩個男生回到原先位置聊起天。我亦扭捏跳上他們斜後方圍欄枯坐,在這之後赤腹總是零星經過,沿著遙遠又高聳的山脈起伏前行。除了鳳頭蒼鷹與遊隼相互追擊之情形使人微微清醒,其餘時間被小群小群分批到來的赤腹衝過或經過涼亭而割裂,我們陷入精神匱乏,IG、FB此時起不了多大作用,連東方蜂鷹掠過涼亭的明亮身影都無法改變呼吸的頻率。兩個男生閒聊著兒時至今的賞鳥經歷,我盡可能使自己不像個局外人的聽著不放過任何從言語中得到群體認同的機會且不留痕跡,但大多數時候,我只能盯著那些其實我根本看不見的個體途經湛藍飛越市區上方,想像牠們沿著中央山脈南南段走勢飛過知本主山與大武山,會有一隻亞成鳥目睹了剛做母親的羌仔虎在山林間為追捕獵物而撞上山豬吊的瞬間(究竟是羌仔虎抑或是羌仔虎),在那一刻牠的瞬膜覆上角膜,同時蓋上困惑的一切,而後,這隻亞成鳥會在墾丁與其他飛越整個西台灣的鷹群會合後再往南國之南,天際線彼端前行。
約莫過了等待山鶺鴒從密林裡現身那麼久,埃圖的虹膜透出一絲躁動不安,背脊微彎的弧度隔著薄到幾乎透光的綠色排汗衫緜延而下,他用望遠鏡快速掃過天空後就拿起相機走到陽光下,有一瞬間我以為他身上會匯流出一條山脈的巍峨。大衛很快就找到埃圖瞄準的位置,出於青少年自尊心,我拒絕詢問,花了一點時間但終究也找到了。從望遠鏡裡望去,遠方無數赤腹鷹有規律地與雲霧交纏,牠們盤旋得又快又高,有些一下子就隱沒在雲裡,接著更多的赤腹鷹從雲的另一端傾洩而出,雖說兩天前才剛看過更大量,但每次見到鷹群我仍會像隻擺出僵直姿勢(Owl concealing posture)的領角鴞,愣怔看著一切發生。不一會兒,好似有什麼力量在牽引著,鷹球緩緩拉長為帶狀鷹河,鷹河流動壯闊且莊嚴,數以百計的赤腹鷹以雙翅承載路途中的風起雲湧朝我們的方向滑翔而來。我們放下望遠鏡開始數鷹,然而事實是,我經驗淺薄,數數結果常與現場其他鳥友相異,且鷹球或鷹柱等盤旋狀態並不適合計數,必須等待鷹河出現,即便如此,人的眼睛仍然跟不上牠們往南的決心。我聽見埃圖和爸爸說,這群用估的吧,三百隻左右。我總是不明白這到底要怎麼估呢?鳥隻數量如此龐大,他們卻總是能計算得與實際數目不相上下。從埃圖家六點多上山一直到中午十一點下山前,總共有兩千一百八十一隻赤腹鷹在遷徙路上經過台東四格山上空或周圍。牠們離開一如來時,鷹球蜿蜒成鷹河,鷹河又盤成鷹柱,在天空裡流淌著自己的節奏,接著又成了鷹河,一隻兩隻三隻,堅定的羽翼亮麗的眼神在秋天裡從不曾停止往南方前進,當牠們離開時,那鷹,那山,那雲,甚至是埃圖,竟同在眼眶裡渺茫起來,也許是因為我總望著他的背影,而他總傾聽遠方的呼吸。
一年前的溽暑,某次賞鳥活動中十五歲的我認識了埃圖,當時他才十九卻已擔任好幾年鳥會解說員,他愛鳥,從小開始賞鳥的他對台灣鳥類瞭若指掌,正因如此,他在一群叔叔伯伯中格外顯眼,直到赤腹鷹過境期結束為止,我盡可能出席每一次活動,也開始學習自己找鳥、辨識鳥,去年光是看赤腹鷹就去了至少十次四格山,我說不清自己到底是為了鳥還是為了偶遇他。看鳥沒有什麼一定的,人必須學習如何接納目標鳥種未出現的失落感,我想我對他也是一樣的吧。他待我時而親近的如同世上只有我能理解他,時而冷靜客觀保持禮貌與友好,我們的關係在山林間生成復又死去,我渴望創造,他以自己的標準維持平衡與秩序,我不知何時會失序,他會是生命中的一隻稀有迷鳥或是同過境鳥一般定期往返而成為留鳥的機率更是如同奢望。走向他的路斑駁老朽,雖平順卻令人惴惴不安。行經泥濘,足跡遂碎裂成數隻安睡於姑婆芋上的莫氏樹蛙,水氣圍繞翠綠的皮膚,碩大的瞳孔在平展的葉面上靜止不動。我用力閉上眼,再睜開,瓦藍的天空下,埃圖就站在那裡,看著我。林間忽起樹濤,葉片間凝結一片綿綿寂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