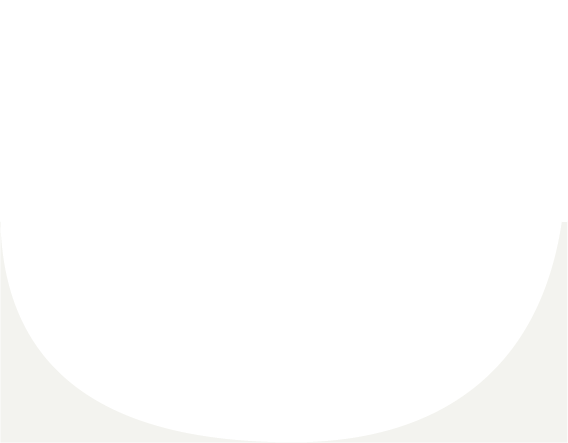works
文學獎專區
歷年資料

奶奶
台中女中
詹佳蓉
奶奶
除夕夜,一年中奔赴各地的家人們終能相聚之時。觥籌交錯,笑語喧嘩,歡愉熱鬧的氣氛彎了眾人的眼角。倏然,一陣爆裂巨響,眾人紛紛向窗外望去,發出期待的驚呼,只見數道尖銳的光亮劃破漆黑沉寂的夜空,絢爛奪目,於下秒綻放剎那芳華。
偌大的房子,沉默一角的東南隅,座落著一方寂寥的空間,與眾人歡鬧的喧囂隔著一扇薄薄的門扉。
年夜飯吃到了最無聊的地方,我無所事事,拿著盛了零食的盤子進了阿金婆的房間。
「阿金婆?」我喚道。房裡光線昏暗,空曠而靜謐,恍若與外頭錯置在同一個時間點卻不同的時空。她正唸經,閉著眼,口中念念有詞。聽見我的叫喚,阿金婆停了下來,睜眼道:「按怎?」
「要不要出去吃東西?」
「毋免,阮猶未餓。」
「那你什麼時候會餓?」
「這馬猶未。」
「喔,好吧。」
我躺到床上滑手機,而阿金婆明明說不會餓,卻放肆的伸手拿我碗裡的食物,害我床都還沒坐熱就要再去補貨。她吃這麼多,卻不幫我去。
窗邊新插的百合染著粉嫩的紅,窗外是漫天煙火消逝後沉寂清冷的夜空,浮華褪盡,如指尖流沙。
阿金婆的真實身份,是爺爺的小三。簡而言之,爺爺當時年輕氣盛、放蕩不羈,不顧懷有數月身孕的奶奶在家,與一名同樣盛氣凌人的女子開啟明目張膽的婚外情。家人們皆無法接受此所謂「喪盡天良」之事,卻無力阻止,只因那名跋扈如潑婦的女子有十足的本事將他們家鬧得烏煙瘴氣。奶奶起初傷心欲絕,爾後也只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習慣了,年幼的爸爸與弟妹全看在眼裡,厭惡極了這個欺負媽媽的女人。而最使家人們無法置信的是,在許多年奶奶過世以後,爺爺竟將她接到家裡同居,再也沒有離去。
不論阿金婆年輕的模樣是否如家人所描述的一般狂傲驕橫、潑辣刁鑽,我看見她的第一眼,其實是完全沒法想像的。她的眼神安靜而祥和,說話時總是同樣不慍不文的語調,和不急不緩的步伐,說不上和藹可親卻又有別於一般冷漠的老人家。她唸佛,吃齋,沉默自適,一個人時口中總是唸唸有詞。我已無法穿透她面容上的褶皺推測其從前的容貌,只在阿金婆房間的抽屜中看過一張老舊的照片,是她年輕時的獨照,唇上抹著張揚的胭脂,是那種刻意又惱人的風流。如果她是我同學,我猜我也會討厭人家。
我們這一輩的小孩稱呼她為「阿金婆」,並不是奶奶,我想這是身分不被承認的象徵。但事實上,我打從出生就沒見過奶奶,阿金婆更像是我真正的奶奶。我也喜歡跟她一起,膚淺的原因是因為她會給我零用錢、請我吃爭鮮,較不膚淺的原因是因為她不像討厭的大人,她總會聽我說話,即使爆粗口也只會呵呵冷笑,她不會批評我買了一堆沒有意義又浪費錢的小東西、不會把我當小孩說教、不會叫我好好讀書或像其他親戚有事沒事就說妹妹越長越漂亮摟。阿金婆真的很怪,好似世界上的一切都無關緊要,但我保證我是她最喜歡的小孩。
她其實也無形中教會了我很多事。直到越長大才越能感受到,阿金婆似乎是內化了許多人生際遇產出的體悟,否則她怎麼能將周遭的空氣沉澱的如此和諧又寧靜?我在猜,也許是她在染盡人間煙火後終究洗煉出了生命的溫潤,但也或許她根本與普通人無異,只是成了一顆孤寂所以緘默的靈魂。
我可以在老一輩家族成員的眼神、話語和許多大小事中體認她是如何不被待見,卻不清楚以前曾發生過怎樣的腥風血雨。爸爸說,阿金婆與家人之間的隔閡,也許是時間無法磨除的。即使過了這麼久,子孫對於她,也僅培養出疏離的長輩禮節。但自我有記憶以來,她似乎也不曾嘗試過融入。或許,她還是藏著一身傲骨,你對她好,她才對你好。
我有時會試圖猜測,不知阿金婆這麼一雙看了世界超過八十年的眼睛,是否早看淡了這一切?我好想體驗一次她的眼睛,來讀懂她對這個世界的詮釋。
在爺爺過世以後,阿金婆一個人待在苗栗的家,鮮少有人探望。只有爸爸媽媽時不時會假借回家的名義和她吃頓飯、聊聊天,這也是我與阿金婆較親近的緣由之一。後來才察覺,阿金婆其實也是個會感到寂寞的正常人。每次到苗栗吃飯,我都多少能感受到她被陪伴的喜悅。
我曾問爸爸,你不討厭她嗎?他老實的回答:「曾經當然是非常討厭的。」
「但現在的阿金婆,只是一名孤單的奶奶。」
某個春日向晚,爸爸開車載著家人從苗栗阿金婆的住處折返回家,她少見的出來外頭送我們離去。
我和她擁抱:「掰掰,阿金婆。」她淺淺的帶笑,也許她今天很開心,開心時也只有半點的笑。
我又向爸爸問起了阿金婆,他竟少見的提了別的內容,多少有種為爺爺和阿金婆平反之感:「其實在那個時代,結婚對象並不是自己能決定的。你爺爺本就不是聽長輩的型,硬是與家裡人對著幹,帶回了阿金婆,重傷了你奶奶。對我來說,她真的很可恨。但到頭來,所有的責怪和辱罵落的是在她頭上,現在也沒有人會陪她了。」
「其實這事兒裡的每個人都有悲傷的。」
我沒回話,只突然想起王國維在《紅樓夢評論》中引用的叔本華三種悲劇之說:「第三種悲劇,由於劇中之人物之位置及關係而不得不然者,非必有蛇蠍之性質與意外之變故也,但由普通之人物、普通之境遇逼之,不得不如是。」但或許這份美化成悲劇的解釋只是在為錯誤套上冠冕堂皇的皮囊,沒看見過去的我,自然而然偏袒了阿金婆。我原想問:「那你認為阿金婆錯最多嗎?」然而終究沒問出口,我想有些事我無從理解,也永遠不能理解。或許爸爸也不曉得。
鄉間顛簸的路徑使車身搖晃不止,我坐在後座,忍不住望向後照鏡,竟見背著斜陽的阿金婆仍站在原地目送我們離去。她的身影單薄而孤寂,帶著淺笑消融後收斂的神情,逐漸縮小、縮小,直至再也看不清她的輪廓。
不知怎的,我霎時紅了眼眶。
爸爸沒有再提起過這份體悟。
想必爸爸也曾掙扎過,是恨,是無視,還是放下。阿金婆做了錯事嗎?她和爺爺是不被祝福的真愛嗎?我無權,也無能討論這一切的是與非,也無法試圖猜測為何在這麼多年以後,她願回到這個明知無法融入、明知不被待見的地方。我不知道,也永遠不會知道爸爸在心中最終的抉擇,只知道他與阿金婆說話時從不提起那段日子,也從未逼問:「你後悔過嗎?」
所幸,遠離陳年往事的我無需在這難題中掙扎,被逼迫詮釋無解的悲傷。我只需看見我所看見的,敬愛我所敬愛的。
同年五月,阿金婆因腎臟疾病住進了醫院。她說她知道自己這個年紀,有很大可能出不去了。提醒我們,如果她到後來成了不能自理的模樣,一定要幫她簽放棄急救書。我這才正式察覺,我們真是阿金婆唯一的親人。阿金婆也是我的奶奶。
不久後,阿金婆便與世長辭,至始至終我都沒見她一點狼狽。她說,喪事要以佛教流程為主,一切從簡。
下葬的那天,天氣溫潤清朗。就連吹來的風,都是那樣平靜,好似從來沒有變。